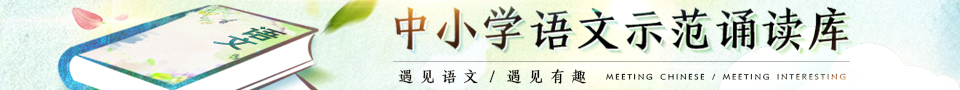语文课堂上的反叛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0.11.23总第973期《中国新闻周刊》
多年来,郭初阳常被拿来和电影《死亡诗社》中的那位疯狂教师做比较。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他讲课的方式称得上与众不同,有人觉得他的课不好理解,但也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听完之后开始着迷文学,“嫌上课时间太短”。
郭初阳是获得多个公开课奖项的明星教师,更是当年语文课本积弊批判大潮中的带头人之一。2008年,他在名声正盛时选择离开执教六年的“名校”杭州外国语学校,随后开始研究语文课本中的诸多问题,此后又到私立机构“越读馆”做语文教学的负责人。
郭初阳并不掩饰自己课堂的“烧脑”,他把语文课比作戏剧表演现场和观看电影《盗梦空间》。早在十几年前,他就会给孩子讲《纽约客》杂志和国外新闻媒体的事实核查员,讲美国作家冯古内特有着古怪幽默和讽刺色彩的科幻小说,讲如何给报社写信投稿,连看了课堂录像的成年人都会惊叹:这个课堂听下来不容易。
见到郭初阳时,他就提到自己刚刚买了新版的语文课本,正在研究,“现在我们肯定看不到过去那种(几个版本可以同时研究的)情况了。”说起这些他有一点淡淡的无奈。早在2009年,他就曾在江苏扬州的“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活动中批评语文课本“短小轻薄”,内涵不够。但是多年过后,在他眼中一切还是那个样子。
70年代生人的自由课堂
多年之后,郭初阳在一次活动中遇见了自己入行时带的第一届学生,其中有个同学对他说:“老师,你还记得你当年对我们说过这句话吗:有我这样的老师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狂傲,但其实,这个当年在萧山浦阳镇的乡村小学附近玩泥巴的小孩郭初阳,从没想到自己会继承母亲的职业成为语文教师。他读书时痴迷数学,因为一次考试失利改学了文科,又在考大学时阴差阳错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大学时,郭初阳和后来同样成为语文老师的蔡朝阳总是坐同桌,对未来的迷茫把有些书生意气的年轻人拴在了一起。那时,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深深影响着这些“70后”,他们最爱做的事就是到杭州三联书店、晓风书屋看书买书,在路边的摊贩手里买打口碟,组起乐队参加校内的比赛,甚至花一个月时间坐绿皮火车去敦煌等地流浪。
“人是有阅读黄金期的”,这句话对郭初阳和他的学生同样适用。从复旦学者郜元宝的《拯救大地》到学者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再到钱锺书的《管锥编》,甚至少年时代阅读的金庸小说,都成为滋养他的文学养分。在大学这个阅读黄金期,他爱上了文学批评,一心要去复旦大学读硕士,结果考研失利,只能去杭州翠苑中学做了语文老师。
初上讲台,一肚子文本的郭初阳没学过心理学和教育学,就直接用大学老师的方法给初中生上课,那种方式,如今他自己想来都显得过于学术:把最精华的文学拿来“一通狂吹”,听得台下的初中生直发愣。他也曾经“略带悲壮”地在社会课上按照自己的设想上过一堂失败的语文课:直接讲《诗经》里的《考槃》和黄宗羲的《原君》,配上《二泉映月》的音乐,内容没什么内在联系,反馈却来得很直接——有位学生大声提问:郭老师,你在教些什么呀?
他想起,胡适谈论过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教师、作家、学者。既然做不了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有研究能力的人或许可以在教学上作出文章,讲授他所认为值得的内容。幸运的是,翠苑中学有两位教育水准极高的同事帮他补上了教育经验的不足,而郭初阳也试着把语文课弄得好玩一些、独特一些,那时他常对学生说:下节课要做一些练习,你们只要考个好分数,咱们就继续一起玩。这个办法居然屡试不爽。
郭初阳在翠苑中学教出了成绩之后,2002年他辞职去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的私立初中部英特学校。“杭外”是一所在全浙江乃至全国都显得特殊的学校,以富有人文气息的自由文化环境知名,其背后是高考政策对外国语学校的优待:它是教育部认定的、享有保送20%学生上大学资格的16所外国语高中之一,初高中一贯制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中考压力。根据该校公布的最新数据,“杭外”平均每年约有50%学生在高考前被国内外大学提前录取。因此,这里的大部分学生可以充分享受到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