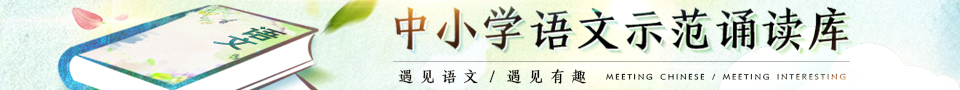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强调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 。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
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如茶道,如医道,如剑道。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现了中容和,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联。两千多年前, 《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尽管古人强调诗词的政治性、社会性,但并不否认诗词的根源在于人性与人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情通过诗词的真情、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达。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但诗不是。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可以说,诗词体现的个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国天下的另外一半。没有这一半,另外一半也不完整。
从统战角度看,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关系密切。
先举几个小史例。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人没
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的诗却是: “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花深院” ,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
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贵族(高昌回鹘) ,但他写的屈原,比汉人写得都
好。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