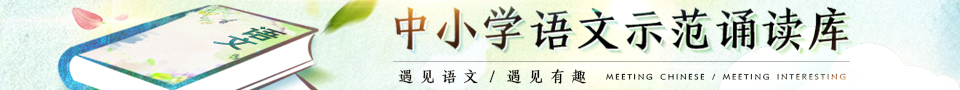这所大学与在成都复学的另外四所教会大学一起
成就了类似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迹
燕京大学的成都岁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19.11.4总第922期《中国新闻周刊》
蔡公期一路颠沛流离抵达成都的那天,刚好是1942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他提着脸盆、网兜,一路打听,找到了燕京大学男生宿舍所在的何公巷1号,即成都文庙。文庙前有两棵参天的大桂花树,其时开得正好,浓香飘逸。从此,他一生都对桂花有特殊的感情。
几天之后的10月1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侵华日军封闭的北平燕京大学正式在成都复学。这所大学与在成都复学的另外四所教会大学一起,被称为华西坝“ Big Five”,成就了类似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迹。
燕园“孤岛”
1941年的燕京大学,如华北沦陷区中的“孤岛”。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纷纷内迁。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日本和美国尚未直接冲突,司徒雷登选择在北平继续办学,“为华北的广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以往挂着中华民国国旗或燕大校旗的高高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
1941年秋,不满18岁的新闻系新生张澍智第一次置身当时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园,只见周围湖光塔影,小径蜿蜒,绿杨垂柳,草坪如茵,感觉无比震撼。
9月2日傍晚,入学第二天,399名新生在临湖轩草坪上集合,与校长司徒雷登及各学院院长握手。今年97岁的张澍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觉得这一刻像签了一份“契约”,让她终身对燕大有了归属感。
开学不久,一张“新生十诫”赫然贴出:“不许昂首阔步,不许出言不逊,不许说方言,不许男生穿西装打领带,不许奇装异服,不许左顾右盼,不许搔首弄姿,不许趾高气扬,不许胡拉关系,不许顾影自怜,不许面目可憎,不许语言乏味。”如有违者,会被“拖尸”(toss)。
这是老生给新生的下马威。违反“十诫”的新生会被抡三下,当众扔进西校门附近一个齐腰深的水池。拖人者都是过去的被拖者,多为“闹将”。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费景汉就曾被扔进湖中。老生们“拖尸”时会事先广播,引人围观,锣鼓喧天而来,心满意足而去。张澍智唯恐有犯,只敢穿蓝布褂,走路低头,目不斜视。
第二周,所有一年级女生都被女体育老师召集到女生体育馆,脱光衣服,依次站在一面大镜前,每人拍一张单人全身侧面像。女生们满心惶恐,却不敢提出异议。两天后,体育馆门口公布了一张名单,每个人的形体都被打出分数,根据分数分班上体育课,如斜肩驼背者上矫形课。张澍智被分在Rhythm(韵律舞蹈)班。
除了国文课,其他科的参考书都是英文原版书。经济学概论、地质、室内装饰、心理卫生、音乐欣赏、中国戏剧小说等选修课都让张澍智大开眼界。按燕大校规,体育不及格就被开除,没人敢旷课,时间久了,她也喜欢上了体育。
每天清晨,她抱着书本,踏着两排松柏间的小路走向教室,幸福而充实。她没想到,这样的时光只持续了三个月。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晨,张澍智的地质课刚开始十几分钟,教室门被几个日本兵推开,所有人被命令去礼堂集合。
白发苍苍的美国老教授没有理会,继续讲课。讲完后,他卷起那幅挂在黑板上的地图,说:“同学们,多保重, 再见了!”他站在讲台上,静静目送每一个学生走出教室。
全部美籍教职员都作为战俘被捕,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等十余名中国师生也先后被逮捕。司徒雷登当时出差天津,也随即被捕。
学校被封,校园被征作日军疗养院,学生们四处流散。
张澍智被日本人和伪派出所强迫转学到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该校已于1937年西迁,参与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习音乐,非常不情愿地去报了到。
华西坝
燕大被封的消息传来,后方群情激愤。
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梅贻琦之弟)在回忆录中记述,1942年2月,燕大临时校董会一致决议在后方复校,他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
一开始,临时校董会考虑在重庆或兰州复校。举棋不定时,汇集在成都的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向燕大发出了邀请。
全面抗战开始后,华西协和大学陆续接纳了西迁而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召开校长联席会议,决定战时实行联合办学。这四校“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
梅贻宝闻讯前往接洽,当地礼遇有加。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尤为支持,校址最终定在成都。